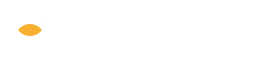长臂管辖(Long Arm Jurisdiction)本是美国内法律界的一个术语,即越过法院所在地而在域外执行法律管辖权。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兴、华为等事件的发酵,长臂管辖已为民众热议。由于长臂管辖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尤其美为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将长臂管辖作为地缘政治武器而滥用时,长臂管辖就超越了法律层面,成为众矢之的。本文在探讨美国长臂管辖的内涵、法理基础及其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对中国实施长臂管辖的动向及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应对举措。
美长臂管辖的产生与发展
域外法律管辖权并非美国专利,但作为域外管辖权的表现之一的“长臂管辖”,则是美国特有的一项管辖权制度。它的制定和适用根植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法律与历史文化背景。作为美国当前国内各地方法院之间划分确定法律管辖权的法律制度,长臂管辖是美在一定国内与国际法依据的基础上,并经过长时间司法实践而逐步累积发展而成的。
传统上,美国民事诉讼分为对人诉讼与对物诉讼。与之相应,美国法院的管辖权也有属人管辖权与属物管辖权之分。在“长臂管辖”产生之前,美国法院属人管辖权的确定,依据的是普通法管辖规则,即以被告在法院地的“实际出现(Physical Presence)”为基础。如被告在法院地有居所或住所、被告出现在法院地,只要该自然人存在于该法院所在州内,并被送达传票,则法院就能对其主张管辖权。该管辖权原则的法理逻辑是:首先肯定每个州对其境内的人和物拥有排他的管辖权与主权(“领土主权原则”),然后,根据某自然人是否只要被告在该州出现(“存在”),来确立是否拥有对其的一般管辖权,这就是传统管辖权所依据的“权力支配”理论。
但是随着社会的互相交流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该原则的缺点日渐凸显:如果有诉讼纠纷的非居民未在法院地“出现”,法院行使管辖权将受各种掣肘,无法采取法律行动。这使传统的管辖权理论和规则受到了质疑和挑战。1945年,美国“国际鞋业公司案”判例,对法院属人管辖权进行了扩展,规定非居民即使不在法院地,但只要其在该地有持续性和经常性活动,且该活动与原告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与这种联系有关,该州法院对被告就具有属人管辖权,即可以对在该州以外的被告发出法院传票。这就是著名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该原则渊源于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该案是美国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管辖权的确定以“最低限度联系”为衡量尺度,被告与法院地州之间的“最低限度联系”取代了传统的“实际存在”原则,成为一种新的管辖权确立依据。这也是长臂管辖权的开端和理论基础。此后,美各州纷纷立法,扩大其司法管辖权,长臂管辖原则遂成为美法律的重要实践和传统,并适用于税收、商业、网络等与法律相关的不同领域。美国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使长臂管辖权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并超出了国界。尤其在对外经济制裁方面,成为美全球霸权的极具威慑力的抓手。
内涵不断扩展升级
全球化时代和当前信息化时代,各国利益高度关联和相互依赖。在此背景下,各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人员与机构往来等等,在社会经济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为长臂管辖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美遂借助这一新的时代条件,根据其内在法理逻辑,对长臂管辖进行了升级扩展,向全球延伸。
一是扩展利用国际法中的“国籍原则”(Nationality Principle,或属人原则),即无论某国居民是在该国领域之外还之内,该国均有管辖权。这是美实施域外管辖的主要法理依据,对此,美在1950年的《对外交易控制规则》等法律文本中,对其“管辖对象”进行了具体规定:美国公民或居民;依据美法律注册的公司;美公民、居民及公司拥有、控制的企业或任何形式的组织。美《1949年出口管理法》及其后继的历次修正案中,则进一步把“属人原则”进行扩展,把除了人员、公司等组织外,任何源自美国的商品、技术等资产,均赋予美国“国籍”。依此规定,但凡美国的技术、产品,即使生产过程中被改变,或者作为外国产品的一部分,其在境外使用或再出口,都受美管辖。1988年,美通过《多边出口管制修正案》,规定如果一国国家违反美基于安全目的实施的出口管制规定,美可对其进行制裁。自此,美明确了其经济制裁立法对第三方具有长臂管辖的权力。
二是客观属地原则(Objective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即效果原则)。这是对国际法中属地原则的扩展,即当国外某行为对国内产生直接、可预见的实质性影响,美即可进行管辖。1987年《美国修订对外关系法重述》中,对此进行了宽泛规定,如果非美国居民有影响美国公民的意图,即使没有实施或没有实际影响,也应受美管辖。
三是保护性原则(Protective Principle),指如某些外部行为威胁美国安全、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美可实施管辖。这些行为包括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犯罪行为、联合国决议限制的行为,以及美认定的“与侵犯人权或财产权的国家的交往”等行为。
四是普遍性原则(Universality Principle),指对国际社会公认的有全球性危害的行为,比如海盗、恐怖主义等,美可进行惩罚和管辖。
经过各种升级、扩展,美国长臂管辖已高度泛化,国际上任何人员、组织、事物、行为等,只要与美国沾边或可能沾边,美均有管辖权。这是极度宽泛的“最低限度联系”原则,给予美国“将手伸出国界”的无限自由裁量权,也为美干预他国、成为“世界警察”和“世界法官”提供了法理基础。
“披上法律外衣”的全球霸权工具
全球化导致全球各国深度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具有不对称性。这为国际关系中复杂相互依赖中的优势一方带来了权力,即其可利用这种非对称性,逼迫对象国改变其政策行为,服从施压国意志。美国作为全球实力超群的大国,在外交、安全、科技、经贸、金融等领域均占据主导地位,为美国利用其在政治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地位,巩固捍卫其国家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提供条件。而长臂管辖权,作为美域外执法与司法的基础,是美以法律形式输出其国际影响力、巩固和推行国际霸权的渠道和手段。与军事干预等对外政策工具相比,长臂管辖拥有法律的外衣,“合法性”更充足。
美长臂管辖常适用于对外经济制裁领域。具体体现为次级经济制裁和三级经济制裁。一级经济制裁(或初级经济制裁)是指限制本国与对象国的经济交往;次级制裁主要是限制本国在境外的组织与个人与对象国之间的往来;三级经济制裁要求本国和外国都断绝与制裁对象的交往,而且还要断绝那些继续同制裁对象有经济交往的行为者。长臂管辖的功效就是将美国海外子公司和第三国公司都纳入到美国经济制裁的管辖范围中来,切断制裁对象通过第三方渠道获取规避制裁的机会。由于美国实行经济制裁的目的和领域越来越多样,除了地缘政治(如与苏联争霸)和意识形态(如制裁古巴等)外,还包括民主与人权、有组织犯罪、反对贪腐、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因此,美对外进行长臂管辖制裁的领域和具体法律也多样化。较典型的包括: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制裁伊朗、利比亚的《达马托法案》;反恐领域的《爱国者法案》;人权领域的《苏丹和平法案》;打击人口走私的《走私受害者保护法案》等等。只要第三国居民或组织触犯上述法案的规定,美国即可以依据“最低限度联系”等原则,对其进行管辖、制裁。
各国反制长臂管辖的主要做法
作为一种“治外法权”,长臂管辖的滥用势必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对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挑战。尤其是美发动长臂管辖的动机日益“泛化”,除了出于地缘政治博弈、国家安全等传统动机,民主、人权、防扩散、反贪、环保、打击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因素也不断被纳入目标之列。这说明,无论是美国的敌人还是友邦,美长臂管辖就像悬在他们头顶上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随地可能遭受其直接或间接冲击。面对美无处不在的霸权,为维护自身的独立与尊严,被制裁国家或受其波及的国家无不斗智斗勇,采取措施予以反制。
排在首位的反击举措,就是从法律上予以反击。美长臂管辖最大的问题是与国际法中的“司法独立”“国家主权”等基本原则相冲突,因此,备受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诟病。一是立法“阻断”美过度延伸的法律“之手”,阻止域外法律在本国司法管辖区内生效。为应对美臭名昭著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达马托法案》等法,欧盟于1996年颁布了“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规定基于制裁的任何外国法院判决或行政决定,在欧盟境内无效;禁止欧盟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居民与企业,依照该法所列出的美国制裁等域外法律来行动,否则企业将面临罚款;允许受影响企业通过欧盟法院向对其施加制裁且造成其损害的域外机构追偿损失。这起冲突以1998年欧美达成政治协议而落下帷幕,双方相互让步,致该法案一直未实质生效。但在美特朗普政府2018年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全面对伊制裁后,欧盟遂重启“阻断法令”,并宣布当年8月生效,以保护欧盟企业的利益,宣示自身主权独立的主张。二是针锋相对,制订反制裁相关法律法规。如俄罗斯为应对美对俄不断升级的贸易与金融制裁,就出台了多项反制裁法,包括2018年6月普京签署并于当月生效的《关于影响(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的法律》。该法明确指出,立法的目的就能是为了回应美对俄公民与组织的不法侵害。
第二,构建专门机制,绕开美国对贸易与金融的控制。美长臂管辖所依托的是其全球霸权地位,普通国家难以与美全面对峙,但可在国家层面设立相关机构,帮助本国企业与居民免受美长臂管辖的影响。比如,2018年2月,委内瑞拉正式发售基于石油的数字货币“石油币”,以之与委交易,可免受美金融制裁的影响。伊朗也同样想方设法开拓渠道,在贸易、金融领域帮助其企业免受美国打压,包括开启黄金与易货贸易制度,即外国可用黄金、日用品等实物,交换伊朗的石油,以及启动“哈瓦拉”(Hawala)等非传统资金转移系统,帮助本国企业完成对外资金的收付与结算。一些国家还通过在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离岸天堂设立“幌子”公司,以第三方公司名义与被制裁国进行交易。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在2018年宣布拟设立独立于美元支付体系的“特殊目的实体” (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 ,帮助欧盟企业与伊朗进行交易。对此,欧洲各国纷纷响应,法、德、英三国随即宣布建立面向伊朗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货币结算机制。该机制总部设在巴黎,其运作类似对敲交易,以欧元结算,但初期主要是涵盖医药等非石油民生物品,以避“与美对抗”之嫌。
此外,国际多边机制也是反制美长臂管辖的重要渠道。面对美国日益突出的单边主义行动,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以多边主义回应其单边主义。美长臂管辖原则是不符合WTO相关规则的,对此,1996年,欧盟曾就《赫尔姆斯-伯顿法案》的威胁,要向WTO起诉美国。这是导致美最终与欧洲妥协的因素之一。
美对华长臂管辖的实践及我国应对举措
美国是全球经济制裁的主要发起者,目前已经对全球约40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进行过制裁。中国也未能幸免,同样是美国制裁的受害者。一是直接对华制裁。如1949年建国后至1971年。二是间接对华制裁,主要就是美利用长臂管辖权,对“触犯”美对外制裁法规的中国企业与个人进行的经济制裁。据统计,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对中国公司进行过2次制裁。布什政府时期,制裁明显增多,达到十多次;第二任期的布什政府对华制裁数量虽有所下降,但制裁我公司数量也接近20家。奥巴马政府延续了美既定政策,中国昆仑银行是该时期标志性的案件,但总体实施制裁数量有所下降。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对我制裁明显加码,力度也加大。其中,制裁华为案是里程碑式的案件,至今仍未结束。
纵观美对我长臂管辖的情况可以发现,美对我制裁的数量与程度,总体上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坏成正比。我建国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美对华实施制裁,197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破冰改善,美对华制裁也随之撤销;特朗普上台以来,随美将中国列为首要对手,两国进入竞争为主的大博弈时代,美对华制裁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已经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手段也较前翻新。2019年4月,美将37家中国大陆企业和学校列入“未经核实”实体的危险名单,虽在法律上不是制裁名单,但对我实质影响较大;2019年5月,美宣布对华为70多个全球子公司进行制裁之后,又将大疆、海康威视等企业纳入管制黑名单。长臂管辖是美实施国际政治意图的政策工具,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美各式花样的制裁将不断增多。近20年来,涉及我国的制裁主要是防扩散类的,包括涉伊朗、朝鲜类的制裁。但近年来,涉及到人权、反腐、网络安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长臂管辖不断增多,如,美近期根据2017年12月签署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我部分人员实施制裁。
面对美今后可能对我国不断升级、扩大的长臂管辖与制裁
首先应扩大改革开放,加大创新发展,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强国家层面应对美国制裁的实力与战略空间。历史表明,凡是针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大国,美发动经济制裁的成本较高,制裁成功率极低,且难以长久持续。
其次,要加强内部团结,凝聚力量、统一思想与对外发声渠道;同时,要有坚定反制裁的决心。
第三,积极拓展国际经济与外交合作,赢取国际支持。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合作网络越健全,包括货币、金融与跨境支付方面的合作,美国制裁中国的政策就越难成功。要充分利用国际多边组织捍卫我方利益,毕竟,美国以国内法为基础的长臂管辖,违反国际公法的“主权独立原则”和WTO等倡导的相关精神。
第四,学习国际反制经验。可学习欧洲、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在面对美国长臂管辖时,保护本国企业的一些做法,比如出台中国版的“阻断法案”、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SPV机构,为我国企业与被制裁对象的经济来往提供渠道等。
第五,我国涉外企业要加强合规经营,以避免不必要的制裁麻烦。
本文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x220.com/news/26222.html